手机式童年带来的社会剥夺、睡眠剥夺、注意力碎片化及成瘾
- 科技
- 2025-04-13 10:18:06
- 15
【编者按】
95后是第一代进入青春期时不断接触互联网的人群,即Z世代。“手机式童年”取代了“玩耍式童年”,构成了这一代孩子的“新童年”:一方面,父母在现实生活中的过度保护,这让孩子无法在成长中获得足够的挑战。另一方面,社会对孩子在网络上的保护不足。这对孩子产生了4大伤害:社会剥夺、成瘾、注意力碎片化、睡眠剥夺。《焦虑的一代》是《象与骑象人》《正义之心》的作者乔纳森·海特讨论青少年身心成长危机的作品,高度依赖手机和社交媒体已经成为一代人的危机,作者呼吁全社会共同行动来改变这场手机带来的精神疾病的流行。本文摘编自该书,澎湃新闻经湛庐文化授权发布。
手机式童年的开端
2007年6月,史蒂夫·乔布斯发售初代iPhone时,把这部作品定义为“支持触控操作的宽屏iPod,一款革命性的移动电话,以及一款突破性的互联网通信设备”。回过头再去看,那时的iPhone相当简单。我怎么也想不到,它会对心理健康构成威胁。2008年,我也买了一部。它堪称一把电子版的瑞士军刀,功能五花八门、面面俱到,可满足我的不时之需。这款手机的设计初衷并非让我沉迷其中或者霸占我的注意力。
随着软件开发工具包的问世,情况很快发生了变化,第三方应用程序可以直接下载并安装到手机上。这一革命性举措标志着新时代的开始。2008年7月,苹果公司发布了App Store,最初仅提供500个应用程序。谷歌不甘落后,于2008年10月推出了安卓应用市场,后于2012年扩展功能,升级为Google Play。App Store发布后仅两个月,应用程序就突破了3000个,2013年更是超过了100万个。Google Play的发展同样不容小觑,其应用程序的数量在2013年也达到了100万个。
随着智能手机向第三方应用程序的开放,大大小小的公司之间展开了激烈的竞争,誓要开发出最具吸引力的应用程序。赢家通常是那些免费提供应用程序,通过广告盈利的公司。从用户角度看,明明有免费的版本可以用,何必还要花钱下载呢?这种以广告为驱动的应用程序的大量涌现改变了移动互联网用户的手机使用习惯。到21世纪第二个10年初期,智能手机已不再单纯仅备不时之需了,它成了各大科技公司争夺用户注意力的平台。
最缺乏自制力、最容易被操控的群体,当然是儿童和青少年,毕竟他们的前额叶皮质尚未发育成熟。从电视机问世以来,孩子们就被屏幕上的内容深深吸引。但电视机太笨重,不能拎去学校,也不能带着出门找小伙伴们玩。在智能手机普及前,孩子们接触电子屏幕的时间还是有限的,所以他们还有时间出去玩,跟他人进行面对面的沟通。然而,像Instagram这种应用程序的迅猛增长的时期,恰逢少年和学龄前儿童将功能手机换成智能手机,这标志着童年的本质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截至2015年,超过70%的美国青少年会随身携带一个触摸屏设备。这些设备更能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孩子们欲罢不能,哪怕跟朋友在一起时也放不下。所以我才把21世纪第二个10年早期定义为手机式童年的开端。
我在前言中说过,手机式童年中的“手机”一词其实是个广义的概念,包括了所有能上网的智能设备。从21世纪最初10年的末期到第二个10年初期,很多设备开始接入互联网,特别是家庭游戏机,如PS3、Xbox 360,这些原本封闭的内容平台都有了广告,以及新的商业激励措施。此外,能高速上网和登录社交媒体的笔记本电脑、网络游戏,以及由用户生成内容的流媒体平台,如YouTube,也都是手机式童年的一部分。手机式童年中的“童年”也是广义的概念,既包括了儿童期,也包括了青少年期。
社交媒体的迭代
社交媒体经历了数轮进化。不过无论怎么迭代,它们大多具备以下4个功能:一是创建个人档案,展示个人信息、爱好等;二是制作内容,即创作并分享文字、图片、视频、链接等,触及广大网友;三是维护人脉,通过关注、加好友、进好友群或聊天组等方式与其他人建立并维持联系;四是与他人互动,基于彼此分享的内容进行交流,如点赞、评论、分享或私信等。典型的社交媒体,如Facebook、Instagram、Twitter、Snapchat、TikTok、Reddit、LinkedIn等,都具备这些特征。YouTube也类似,只是在用户心中,它更像一个全球视频资源库,而非社交平台。现在流行的视频游戏流媒体平台Twitch也具备上述特征。当代的成人内容网站甚至都不例外。然而,WhatsApp和Facebook Messenger等即时通信应用程序并不完全具备这些特征。尽管它们具有社交属性,但通常不被视为社交媒体。
2010年左右,社交媒体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种变化对年轻人产生了更多的负面影响。Facebook、Myspace和Friendster都成立于2002—2004年。早期,这些服务还被叫作社交网络。因为它们主要是连接单个的人,如找回多年未见的高中朋友,或让某个音乐家的“粉丝”能够相互联系。但在2010年左右,随着一系列创新功能的出现,这些服务有了质的改变。
2009年,Facebook先推出了划时代的“点赞”功能,Twitter则推出了“转发”功能,其他平台纷纷效仿。一时间,各种内容实现了病毒式的传播。这不仅量化了帖子的受欢迎程度,还促使用户为了追求更大范围的传播而精心设计每一条动态。有时大家不得不爆点“猛料”,用极端言论吸引眼球,或者刻意传播愤怒和厌恶。同时,Facebook开始用算法来推送内容,其他平台也竞相模仿,以期通过精准的内容推送吸引用户。2009年,推送通知功能上线了,各种动态可以被实时推送到用户手里。应用商店则带来了新的以广告为驱动的平台。2010年,手机又有了前置摄像头,从此自拍变得易如反掌。宽带网络也走进了千家万户,截至2010年1月,已覆盖61%的美国家庭,用户可以畅快地使用所有互联网服务了。
到21世纪第二个10年的初期,原本以人与人之间的连接为主要功能的社交“网络”系统,转变成了以追求公众认可为主要目的的社交“媒体”平台,这些平台鼓励用户进行一对多的公开表演,以获取来自朋友乃至陌生人的认同和肯定,即使是那些不经常发布内容的用户,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这些应用程序设计的激励机制的影响。
通过这些变化,我们就知道,为什么童年大重构会始于2010年前后,且大体完成于2015年了。父母过度保护孩子,于是孩子被困在了家里,他们变得孤独无聊,越来越容易转向唾手可得的智能设备,里面的内容和服务更是层出不穷,异彩纷呈,孩子们便越陷越深。玩耍式童年由此谢幕,手机式童年一统天下。
手机式童年的机会成本
6~8小时,这就是青少年每天耗在电子屏幕上的时间。没错,早在智能手机和互联网入侵我们的生活之前,孩子们就已经花很多时间在电视和游戏上了。一项长期调查显示,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青少年每天看电视的时间就已接近3小时。在那10年间,绝大多数家庭开通了拨号上网,21世纪初宽带又开始普及,于是人们上网的时间持续增加,看电视的时间则不断减少。未成年人电子游戏玩得多了,书和杂志看得少了。种种因素加在一起,孩子们便进入了大重构时期。更不用说手机式童年开始后,他们在原来的基础上,每天又增加了两三个小时的屏幕时间。这些数据根据社会阶层(低收入群体增加的屏幕使用时间更多)、种族(非洲裔、拉丁裔多于白人和亚裔)和性别认知(性少数群体多于传统群体)等略有差异。
跟实际情况相比,这些数据可能还太保守了。皮尤研究中心换了个问法,就发现有1/3的青少年几乎总是保持登录一个主流的社交媒体。45%的青少年报告称自己“几乎不间断”地上着网。表面上看,青少年每天“仅”花了7小时在网上娱乐。但如果把那些一心二用的时间,即一边做着其他事一边又挂念着社交媒体的时间都算上,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能有将近一半的青少年说自己“几乎不间断”上网。算算看,那相当于每天16小时,每周112小时,孩子们心不在焉,注意力根本不在手头的事情或周边的情况上。按理说,这种不间断的玩法要求孩子有两三台设备才行,如电脑、游戏机。要不是智能手机等便携设备,这种状态根本无法实现。而它一旦实现,便给孩子的认知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让他们高度成瘾,还对大脑路径的形成产生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在青春期尤甚。
梭罗在其文学作品《瓦尔登湖》里聊到俭朴的生活,他写道:“消费一个东西时,你真正付出的成本是……生命的长度,无论你是立即付清,还是慢慢支付。”孩子们每天在电子产品上花费6小时或8小时,甚至16小时,为此付出的机会成本是什么呢?那些对成长来说至关重要的活动,他们是不是已经错过了?
伤害之一:社会剥夺
孩子需要和伙伴们一起面对面地玩耍,以提高社交能力。但如第2章所讲,“几乎每天”都能和朋友一起玩的学生的比例,自2009年起呈显著下降趋势。
当然,青少年是不会察觉到自己在远离朋友的。他们觉得自己只是把友谊的舞台从现实世界搬到了Instagram、Snapchat和网络游戏而已。那不是挺好的吗?其实那并不好。正如心理学家琼·特文吉所展示的,青少年在社交媒体上花的时间越多,越容易出现抑郁、焦虑或其他障碍;而参加同龄人的集体活动越多,比如团体性的体育运动或宗教活动等,孩子的心理就越健康。
这是有道理的。孩子们需要参加面对面的、实时的、具身性的玩耍活动。最好的玩耍场所在户外,偶尔包含一些冒险和刺激的元素。跟朋友视频聊天也不错,这其实就像是传统的电话通话,只是多了可视化的功能。但如果孩子只是孤零零地待在房间里,刷着流媒体推送的动态;或者无休止地玩电子游戏,游戏里的队友和对手还一会儿就换一拨;抑或是自己发表一些内容,然后眼巴巴地等着其他孩子(甚至是陌生人)点赞或评论,那就不好了,这对他们的成长和健康着实无益。这些活动吞噬了孩子大量的时间,侵占着本可以和朋友共度的时光。
童年大重构带来的社会剥夺效应极大,不只剥夺了孩子和朋友一起玩耍的时间而已。就算孩子们见到了朋友,彼此相距咫尺,受手机式童年的影响,他们共度时光的质量也大大下降。兜里的手机振动几下,他们就会立刻停止聊天,把视线从朋友身上转移到手机屏幕上,生怕错过了什么重要的信息。此时他们倒不会让朋友住口,只是会默默低下头,轻叩手指,认真阅读手机里的内容。正在说话的朋友自然就会失落,觉得自己不如这条信息重要。两个人在对话时,只要其中一个人掏出了手机,或者他身旁放着一部手机,可能都不是他自己的,那么这场沟通的效果、两人间的亲密度就会大打折扣。随着显示技术从口袋走向手腕,甚至进入头戴设备和护目镜,人们全神贯注地跟面前的人沟通的能力越来越弱。
无论什么年龄,被他人忽视都是一种痛苦。而青少年正在形成自我认知,寻找归属感,但身边的每个人都在间接地提醒他,他无足轻重,跟手机里的人比不了。再看看年幼孩子的情况。2014年,《高光》(Highlights)杂志进行了一项调查,发现6~12岁的儿童中,有62%的孩子表示,每当自己想跟父母交谈时,父母总是心不在焉,最大的原因就是看手机。父母也知道自己对不起孩子。2020年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68%的父母承认,他们在陪伴孩子时,偶尔或常常会因为手机而分心。在年轻的父母以及受过高等教育的父母群体中,这一比例更高。
童年大重构摧毁了Z世代的社交生活,因为智能手机可以把Z世代的孩子与全世界的人都连接起来,却唯独隔绝了身边的人。一位加拿大的大学生在给我的来信中写道:
Z世代是孤独的一代。我们的友谊很虚浮,我们的爱情很脆弱。这些关系深受社交媒体的引导和牵制……你不难发现,大学校园里早没了社群的概念。当我走进上课的教室时,常常看到30多个学生一言不发地待着。教室里静悄悄的,每个人都刷着手机。没人敢发出声音,好像生怕被别人听到。环境越安静,我们就越疏离,自我认知和自信心的建立更是无从谈起。我对这种体验再熟悉不过,因为我是其中的亲历者。
伤害之二:睡眠剥夺
上学的日子里,为了让孩子按时睡觉,父母们总是绞尽脑汁,而智能手机的到来,让这场“恶战”更难打了。人的生物钟会变,进入青春期后睡得更晚些。但第二天的起床时间是由学校上课的时间决定的,孩子无法睡懒觉。从大脑和身体的需求来说,大多数孩子没睡够时间。这实在是可惜。因为不管在校内还是在校外,学生想表现优异,充足的睡眠都是必要条件,尤其是在青春期,大脑正在快速发育,神经重构的速度远快于之前。跟睡眠充足的孩子比,缺乏睡眠的孩子总是无法集中注意力,记东西也慢半拍。他们的学习成绩因此受到影响。他们的反应速度、决策力和运动技能也会下降,这增加了他们发生意外的风险。他们整天烦闷,动辄生气或焦虑,人际关系也因此受到影响。长期睡眠剥夺还会损害更多生理机能,导致体重增加、免疫抑制等健康问题。
未成年人需要的睡眠时间比成年人多。进入青春期前,每天至少要睡够9小时;进入青春期后,至少要8小时。早在2001年,一位知名的睡眠专家就指出:“所有孩子一进入青春期就成了夜猫子,他们的睡眠时间太少了。”
从发生的时间上看,睡眠时间的减少和手机式童年的开端刚好重合。这只是个巧合吗?还是说两者本就有关联呢?不少证据证明,关联的可能性极大。一篇针对36项相关性研究的综述报告发现,对社交媒体的重度使用与睡眠时间的减少是强相关的;而且,前者与心理健康问题的出现也强相关。该综述还指出,如果人在一段时间内重度使用社交媒体,那么接下来一段时间就极有可能出现睡眠问题以及心理问题。一项实验发现,上学期间,青少年连续两周晚上9点以后不用或少用手机的话,睡眠时间会显著增加,入睡时间会提前,且在需要集
中注意力或快速反应的事情上能表现得更好。另有几项研究采用了不同的设备或活动做实验,包括电子书、电子游戏和电脑等,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夜里用智能设备用到太晚,会干扰睡眠。所以,重度使用电子设备和睡眠剥夺不仅是相关而已,两者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因果关系。
这种因果关系很符合大家的直观感受。特文吉和同事们研究了英国的一个大型数据集后,也得出结论:“重度使用网络媒体与睡眠时间的缩短、入睡困难、频繁夜醒现象有关。”那些躺在床上刷社交媒体或上网闲逛的行为对睡眠干扰最严重。
干扰Z世代睡眠的不止社交媒体这一个因素。手机里还有很多好看、好玩、好入手的事情,它们都是睡眠剥夺的“要犯”,如手机游戏、流媒体视频等。奈飞的首席执行官曾在投资者会议上针对竞争局面说道:“大家都懂的,观众只要看了一点儿我们的节目就会上瘾,就想熬夜看下去。一定程度上讲,我们的竞争对手是睡眠。”
青少年的大脑正在飞速发育,此时若遭遇睡眠剥夺,将产生怎样的后果呢?有一项名为“青少年大脑的认知发展研究”的调查可以给我们提供答案。调查团队于2016年扫描了超过11 000名9~10岁儿童的大脑,并对他们进行跟踪调查,持续观察他们在青春期、青少年期的表现。基于这项庞大的研究工程,专家们发表了数百篇论文,其中就不乏针对睡眠剥夺的研究。比如,2020年的一项研究发现,睡眠干扰的加重和睡眠时间的缩短,与严重的内化行为(包括抑郁)和外化行为(包括暴力攻击,以及由冲动造成的其他反社会行为)呈正相关关系。这项研究还发现,研究初期的睡眠干扰程度能够“显著预测”一年后抑郁情绪及内化和外化问题的严重性。简言之,一个睡不够或睡不好的人更可能抑郁,或者出现行为方面的问题。这种影响对女孩更加明显。
所以,儿童和青少年必须获得充足的睡眠,以促进大脑的健康发育,让第二天有良好的注意力和身心状态。一旦睡前可以玩电子设备,尤其是手机这种可以趴被窝里玩的小屏幕设备,孩子们就会忘记时间,玩到深夜。再看看这场席卷全球的心理大危机,电子设备造成的睡眠剥夺很可能就是背后的元凶之一。
伤害之三:注意力碎片化
1961年,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的短篇小说《哈里森·伯格朗》(Harrison Bergeron)出版了。故事背景设定在一个极端平等的未来时代。那时的美国已通过宪法修正案,规定任何人都不得比其他人更聪明、更有魅力或更强壮。“助残会会长”是一名政府官员,负责强制执行全民平等政策,确保所有人的能力、权利都相等。智商过高的人必须时刻佩戴一个干扰耳机。耳机大约每20秒就会发出噪声,打断人的思考,使其思维能力降至大众的平均水平。
几年前我开始和学生们讨论,手机对他们的学习和工作效率有何影响。当时我就想起了这个故事。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发短信逐渐成了年轻人主流的沟通方式。他们习惯将手机调到振动模式,导致手机一整天振个不停,尤其是参与群聊时。但实际情况远比我想的还要糟糕。大多数学生会接收到几十个应用程序的通知,包括消息应用程序(如WhatsApp)、社交媒体(如Instagram、Twitter),以及各种新闻网站。这些网站会用“突发新闻”字样来提醒学生们关注政治、体育新闻,以及名人的私生活动态。我的MBA学生大多是快到30岁的人,他们还有像Slack这样的办公应用程序。大多数学生还设置了邮件提醒,每封电子邮件送达时手机也会振动。
一项调查称,一个年轻人的手机每天能从用得最多的社交和信息应用程序中收到约192次通知。青少年平均每晚的睡眠时间只有7小时了。如此算来,在他们醒着的时间里,平均每小时会收到约11次通知,相当于每5分钟就有一次。这还没算其他应用程序。其他应用程序如果没关闭推送功能,还得再加上好几十个振动的源头,用户注意力被扰乱的次数大幅增加。这还只是普通青少年的情况。如果我们聚焦于重度用户,如频繁使用短信和社交媒体的青春期女孩,其使用手机的频率高达每分钟一次。科技公司在商战中用尽手段,把青少年本就不多的注意力剥夺殆尽,将冯内古特笔下怪诞的环境设定,带到了Z世代的现实生活里。
1890年,美国杰出的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把注意力描述为“在几个并行的潜在目标或思想碎片之中,意识突然提取了其中一种,使其呈现出清晰鲜明的形象……它意味着为了有效处理一些事情,我们要放弃另一些”。有了注意力,我们才能在诱惑的包围圈中坚守住最初的选择,专注于一项任务、一条线索或一种思维。反之,若思路任由其他事情打断,我们就无法专注,陷入“困惑、迷茫、心不在焉”的状态。
互联网也侵入了阅读的世界,我们已经把大半阅读转移到了线上,保持专注变得难上加难。超链接埋伏在文章各处,招摇地引诱我们走上岔路,放弃对正文的阅读。尼古拉斯·卡尔(Nicholas Carr)在2010年出版了著作《浅薄》(The Shallows),书名真是一针见血。他在书中哀叹,自己已无法专心致志地做事了。互联网颠覆了他的大脑检索信息的方式,他甚至无法离线阅读,还是会分心。他不能再如往昔般集中注意力和反思问题,因为他已对持续的刺激上了瘾:“以前,我戴着潜水呼吸器在文字的海洋中缓缓前进。现在,我就像一个摩托快艇手,贴着水面呼啸而过。”
卡尔写作这本书时,描述的还是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最初10年的事,那时用的上网设备是电脑。他偶尔会提起的黑莓手机和iPhone,都是在书籍出版的前几年才流行起来的。要说破坏力,它们跟后来那些振个不停的智能手机完全没法比。电脑页面的超链接毕竟被动,需要人动手点击才行,诱惑力还是有限。推送和流媒体极具破坏性。每个应用程序都像是一个岔路口;每条通知都如拉斯维加斯的霓虹招牌般魔幻,引诱着你停下脚步:“点击这里!我马上告诉你别人刚刚对你说了什么。”
无论成年人在这场注意力大战中多么力不从心,都没有青少年那样举步维艰。因为他们的前额叶皮质还未发育成熟,拒绝诱惑的能力非常弱。詹姆斯描述道:“孩子们对即时的感官刺激异常敏感,没有抵抗力……孩子似乎更容易被周围的事物所吸引,而非由自己的意志所控制。”让学生们把分散的思绪收回来,是“老师们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所以在上学的日子里,学校有必要用手机储物柜或上锁的袋子,彻底锁住学生们的手机。应用程序的开发者的目的本就是用“即时的感官刺激”来吸引孩子的注意力,他们在这方面非常擅长。
电子产品无休止的干扰,让思考不停地中断或转向,持续地使注意力碎片化。这一定会阻碍孩子思维能力的发展。他们的大脑正在快速重构,这种注意力模式可能会在神经系统中留下终生的印记。许多研究发现,那些在课堂上可以使用手机的学生,对老师的话就不那么专心了。人类的大脑并不支持真正的多线程工作,表面上的多任务协同,其实只是在各个任务间快速切换注意力而已,而每次切换都在无形中浪费了大量注意力。
就算学生没有拿起手机,只是知道手机在附近,注意力也会受到影响。在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将一群大学生带进实验室,随机安排他们将手机放在不同的位置。有些学生是把包和手机放在实验室外的入口处,有些是把手机放在口袋里或随身的包里,还有些将手机放在眼前的桌子上。然后,研究人员让学生完成测试,考察他们的流体智力和工作记忆能力。比如,记住一串字母,并解答数学问题。结果显示,手机被放在门外的学生表现最佳,手机摆在眼前的学生表现最差,手机放在口袋里的表现介于两者之间。这种对比在重度使用者中更加明显。这个研究的报告标题是《脑力流失:智能手机的存在会削弱可调动的认知能力》。
整个儿童时期,大脑都在发育,到青春期会显著提速。孩子们在中学阶段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培养“执行能力”。这要求他们能根据目标制订计划,然后切实落地。执行能力不易提高,因为它非常依赖前额叶皮质,而前额叶皮质在青春期经历重要的发展变化,是整个大脑重构工程的“收官之作”。执行能力的发展需要极强的自我控制力、专注力和抗干扰能力。手机式童年起到的很可能是反作用。如果孩子只是偶尔用一下手机,我还不能断言一定有害。但对于重度用户来说,我们确实一致观察到了更糟糕的结果,部分原因在于这些用户往往在某种程度上对手机上瘾了。
伤害之四:成瘾
当我的女儿发现自己无法将视线从我的iPad上移开时,她的大脑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呢?桑代克在他的时代还不了解神经递质,但他的推测是正确的。大脑的确会对重复出现的小奖励、小刺激印象深刻,能记住这些反应路径。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如果一个动作能给我们带来积极的结果,比如令我们吃到东西、减轻疼痛或者达成目标,那么与学习相关的神经回路就会分泌多巴胺。这是一种与快乐和愉悦感相关的神经递质,我们非常受用,于是大脑就记住了这个动作及其结果。但这不是一种让我们感到满足并减少渴望的被动奖励,相反,多巴胺会让我们产生“欲望”,让大脑觉得“那种感觉真棒,我还要”。当你吃薯片时,每吃一片就能获得一小剂多巴胺,所以你才会特别想吃下一片,欲望比吃上一片时更强烈。
赌场里的老虎机是一样的原理:赢钱带来的感觉很棒,但这并不会让赌徒就此满足地收手回家,反而会激发他们继续赌博的欲望。与此类似的还有电子游戏、社交媒体、线上购物等服务。人们流连忘返,常常不自觉地投入比预期更多的时间和金钱。这种行为成瘾的神经学原理与化学物质(如可卡因或鸦片类物质)的成瘾还是有区别的,不过它们都与多巴胺、欲望、冲动,以及我女儿描述的那种无力感和失控感有关。这种情况是被人刻意设计出来的,应用程序的开发者穷尽了心理学的成果,就像老虎机吸引赌徒那样,让用户深深着迷于这些应用。
需要明确的是,绝大多数使用Instagram或玩《堡垒之夜》的青少年并没到成瘾的程度。但他们的欲望同样被牢牢地捆绑住了,行为受到了极大的操控。没错,广告商们一直在努力做到这一点,但总是差点火候。现在有了触控屏和互联网,各种行为诱导技术得到了极大的扩展。这些技术最适合用来实现快速的“行为加奖励”机制,用户在一轮轮的循环里沉沦。斯坦福大学教授B.J.福格(B.J.Fogg)对这一现象进行了考察,于2002年出版了著作《福格说服技术》(Persuasive Technology)。福格开设了一门“说服技术”的课程,教授针对动物的行为诱导技术,以及这些技术在人身上的应用。后来他有许多学生进入了社交媒体公司工作,有学生甚至还创立了社交媒体公司,其中就包括Instagram的联合创始人迈克·克里格(Mike Krieger)。
容易上瘾的产品是如何吸引青少年的呢?我们假设一下,此刻正有个12岁的女孩坐在自己的书桌前,努力地理解光合作用,因为第二天有科学课的考试。Instagram要怎么做才能诱导她放下书本,持续沉迷一小时呢?应用程序的开发者通常会采用一个4步流程来创建一个能自发反复循环的行为模式,即“上瘾模型”。
当开发者想把一个习惯深深地植入用户大脑时,只需要按照上瘾模型的指导,按部就班地把4步循环过程设计出来即可。
这个循环从外部触发开始,比如发一条通知,告诉用户刚刚有人评论了她发的帖子。这是第一步,这个通知就像一条岔路,引诱她离开正路。通知一出现在手机屏幕上,用户便立刻被激励起来,想采取行动,执行一个动作。这就是第二步,即轻触通知,进入Instagram。用户记得,这个动作曾经让自己得到过奖励。接下来是第三步,即一件愉快的事情要发生了。注意,这一步不是每次都会有的,它的发生概率不稳定,是一个随机的奖励,她可能会收到赞美或友好的评论,也可能不是。
这是行为心理学的一个关键性理论:最好不要每次动物做出你期望的行为时,你都给予奖励。如果你以一个不固定的频率奖励动物,比如平均每10次奖励1次,但有时不到10次,有时又要超过10次才给予奖励,这样,你会在它身上培养出最强大和持久的习惯来。当你把一只老鼠放进一个笼子里,它已经学会按压杠杆来取食。它会在期待中获得多巴胺的刺激,跑到杠杆处按压一番。即使最初几次按压没有得到食物,老鼠也热情依旧。老鼠继续按压,多巴胺水平不降反升,在它心里,奖励随时会降临!食物终于出来后,老鼠心花怒放,高水平的多巴胺会促使老鼠继续按压,巴巴地期待着下一次奖励……在未知次数的反复按压之后,奖励一定会到来,因此,它会继续按压。应用程序中的无限信息流没有尽头,用户一旦开始滑动屏幕,就没有停下来的信号。
以上三步就是经典的行为主义思路,运用了B.F.斯金纳(B.F.Skinner)在20世纪40年代教授过的操作性条件反射理论。上瘾模型额外为人类增加了第四步——投入。这一步在老鼠身上并不适用。投入就是人类在应用程序上花的心思和费的工夫,可以增强产品和用户间的情感。前文提到的那个12岁的女孩在Instagram上创建了个人档案,上传了自己的许多照片,并与所有朋友以及数以百计的陌生用户建立了联系。与此同时,她的哥哥也在隔壁房间备考,已经花了数百小时玩《堡垒之夜》和《使命召唤》(Call of Duty)等电子游戏,并乐此不疲地攒勋章,买“皮肤”或者进行其他投入。
投入行为完成后,下一轮循环又要开始了。但这次已无须由外界提供刺激,她不再需要由一条推送通知来提醒自己打开Instagram了。当她反复学习一个很难的章节时,有个念头突然出现在她的脑海中:“我20分钟前发了张照片,不知道有没有人点赞?”于是,一个极具诱惑力的岔路出现了,第一步完成。她试图抵制诱惑,继续专注于学习,但是光想想可能的奖励,就触发了多巴胺的分泌。她忍不住了,立刻就想打开Instagram,渴望将她的大脑淹没。她果然打开了Instagram,第二步完成。结果她发现,这张照片并没有得到任何人的点赞或评论。她有点失落,但她那被多巴胺刺激着的大脑仍然渴望奖励,所以她开始翻看起自己其他的帖子、私信或任何能证明别人关心自己的内容,以及任何能快速提供娱乐价值的事情。她还真找到了,于是第三步完成。她滑动屏幕,时不时给朋友留个言。不一会儿,果然就有朋友回应了,给她的上一条帖子点了赞。一小时后,她终于回到了关于光合作用的复习中,但已精疲力竭,难以再集中注意力了。
一旦用户自己的情绪足以触发一种行为,这种行为又能得到一个不确定的奖励,那么用户就“上钩”了。现在我们知道了,Facebook在刻意使用行为诱导技术,吸引青少年频繁访问。我们要感谢弗朗西丝·豪根(Frances Haugen),她在2021年披露了一套Facebook的文件。那是一批内部文件和演示文稿的截图,其中有一个部分令人不寒而栗。三位Facebook员工做了一场演讲,题为《身份的力量:青少年和年轻人为什么选择Instagram》。演讲的目的是“协助Facebook公司为一系列产品制定策略,大力吸引年轻用户”。其中一个名为“青少年相关知识”的部分深入探讨了神经科学的发现,展示了大脑在青春期逐渐成熟的过程和原理,指出前额叶皮质要到20岁以后才能成熟。演讲者后来还展示了一张大脑的MRI(磁共振成像)图像,并配有图片说明:
青少年时期,大脑能完成约80%的发育,剩下的20%是前额叶皮质……在此阶段,青少年高度依赖他们的颞叶,这里掌管着情绪、记忆、学习以及奖励系统。
随后的一张幻灯片展示了Facebook努力在用户头脑中创建的体验循环机制,并指出了用户心智的脆弱性。
看了这些幻灯片你就能明白,演讲者不是要保护处在困境中的年轻女性,并非想帮助她们免受过度使用和成瘾的危害。恰恰相反,他们是为了向Facebook的其他员工提供建议,引导大家通过提供奖励、新奇体验和情绪价值,让女性用户更加沉迷。他们提供的建议包括简化青少年开设多个账号的流程,实施更精准的算法,给用户推送更感兴趣的内容。
斯坦福大学成瘾研究专家安娜·伦布克(Anna Lembke)在其著作《成瘾》(Dopamine Nation)一书中,介绍了病人的成瘾经历和原理。这些病人对多种药物或行为成瘾,包括赌博、购物、性行为等。进入21世纪第二个10年后,患者中出现了对网络成瘾的青少年。对数字生活成瘾的人如果不泡在网上,“那么无论干什么都没劲”。这是因为大脑为了适应长时间的高水平多巴胺,会通过多种方式进行自我调节,以维持体内平衡,其中最重要的改变就是减少多巴胺的传递。为了重新获得快感,用户需要增加药物的剂量。
一旦成瘾者的大脑做出了调整,药物带来的愉悦作用就会被抵消或压制。此时用户已没有回头路,只能不断地加大剂量,否则大脑就会进入一种“缺失”状态。如果多巴胺的分泌带来的是快乐,那么它的缺失就意味着莫大的痛苦。离开药物后,平凡的生活会变得乏味,甚至成了一种折磨。除了药物,其他一切都无济于事。成瘾者产生了戒断反应,需要坚持足够长的时间不使用药物,让大脑恢复到其原始状态,这种戒断反应才会逐渐消退,这通常需要几周的时间。
伦布克指出:“无论成瘾的源头是什么,戒断反应的基本症状都是焦虑、易怒、失眠和心境恶劣。”心境恶劣是欣快的反义词,指一种整体性的烦闷与不满。重度使用社交媒体或对电子游戏上瘾的青少年一旦离开了自己的设备,就会有这样的感受,这也是父母和临床医生观察到的。有网络游戏障碍的人进入戒断状态后,就会出现悲伤、焦虑和易怒等症状,这些都是医生做出诊断的关键指征。
伦布克列出的戒断基本症状还解释了成瘾为何会加剧其他三种伤害。最显而易见的是,那些沉迷于屏幕活动的人更难以入睡,这不仅是因为这些活动挤占了睡眠时间,还因为近在咫尺的屏幕发出的强烈的蓝光在误导大脑:“现在是早晨,别再分泌褪黑素了!”此外,普通人夜间虽然也可能多次醒来,但能迅速再次入睡,而成瘾的人往往会抓起手机,点开屏幕开始滑动。
伦布克写道:“智能手机是现代社会的皮下注射针,全天24小时不间断地给人们注射数字多巴胺。”这个生动的比喻能帮我们理解,为什么手机式童年取代玩耍式童年会带来如此毁灭性的影响,以及为什么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初期,这场危机会汹涌而来。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千禧一代的青少年通过家里的电脑,也能接触到各种成瘾的活动,一些人确实上瘾了。但他们不能带着电脑到处走。大重构之后,这个限制被解除了,下一代青少年实现了随时随地上网的自由。
要了解智能手机雄霸天下后的威力,不妨先想象一下,一个睡眠不足、焦虑、易怒的学生在学校会怎么跟同学相处。情况大概率是不妙的,尤其是如果学校允许学生带手机来上课。午餐时间和课间休息,她可能都会争分夺秒地“刷”社交媒体,而不是跟同学进行实时的、面对面的互动,这样的活动才能促进她的社交能力的发展,否则她与同学会越来越疏离,她也会更加孤独。
接下来再想象一下,这个睡眠不足、焦虑、易怒,还社交孤立的孩子做功课的时候又是什么样子。她试图专心,但手机就在眼前,屏幕朝上,不断吸引着她的注意力。她的执行能力已严重受损,铆足了劲也只能专注一两分钟。她的注意力是碎片化的,整个意识都陷入了詹姆斯形容的“困惑、迷茫、心不在焉的状态”。
21世纪第二个10年的初期,我们把智能手机交到了儿童和青少年手里。科技公司乘虚而入,从早到晚地利用可变比率强化的手段训练孩子的心智,如同训练老鼠一样。而此刻,孩子们正处在人生最敏感的时期,他们的大脑正在经历高速重构。科技公司“不遗余力”,设计出成瘾的产品,以此在孩子们的大脑里刻下了许多条深深的路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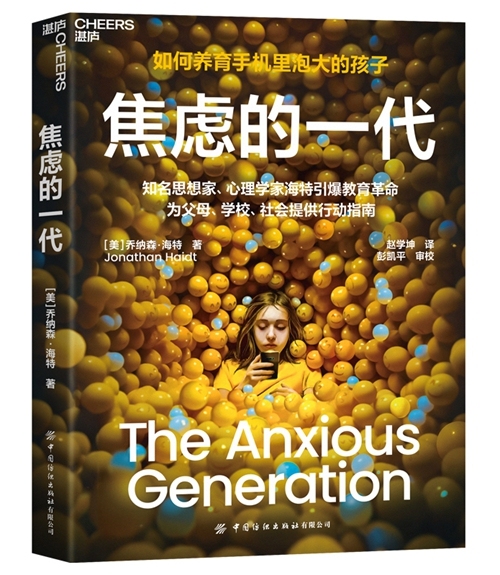
《焦虑的一代》(The Anxious Generation),[美]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著,赵学坤译,彭凯平审校,湛庐文化|中国纺织出版社2025年3月。
下一篇:香港生产力局成立“出海服务中心”
















有话要说...